жҲ‘зҡ„ж–ҮеӯҰеҲӣдҪңеј•и·ҜдәәвҖ”вҖ”иҙәдә«йӣҚ
ж–Ү/д»»е°ҸжҳҘ
2019е№ҙ10жңҲ28ж—ҘпјҢз”ұгҖҠдёӯеӣҪдҪң家гҖӢжқӮеҝ—зӨҫгҖҒеӣӣе·қзңҒдҪң家еҚҸдјҡгҖҒеӣӣе·қзңҒзӨҫдјҡ科еӯҰйҷўдё»еҠһпјҢдёӯе…ұжё еҺҝеҺҝ委гҖҒжё еҺҝдәәж°‘ж”ҝеәңе’Ңдёӯе…ұиҫҫе·һеёӮе§”е®Јдј йғЁжүҝеҠһзҡ„вҖңиҙәдә«йӣҚд№Ўеңҹе°ҸиҜҙеҲӣдҪңйҒ“и·Ҝз ”и®ЁдјҡвҖқеңЁжё еҺҝдёҮе…ҙй…’еә—дёҫиЎҢгҖӮжҲ‘еә”йӮҖеҸӮеҠ дәҶз ”и®ЁдјҡеҗҺпјҢеҗ‘еҚ•дҪҚз”іиҜ·е…¬дј‘еҒҮ5еӨ©пјҢеұҖй•ҝз”іжё…еӢҮеҗҢеҝ—жү№еҮҶжҲ‘иҖҚе…¬дј‘еҒҮж—¶й—ҙдёә11жңҲ4ж—ҘвҖ”11жңҲ8ж—ҘгҖӮ11жңҲ3ж—ҘпјҢе‘Ёжң«пјҢжҲ‘жҠҠ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зҡ„гҖҠд№Ўжқ‘еҝ—гҖӢ10еҚ·еӨ§дҪң规规зҹ©зҹ©е®үзҪ®еҲ°жҲҗйғҪд№ҰжҲҝеҗҺпјҢе°ұеҲ°дәҶдёңй—ЁеёӮдә•зҡ„жқҺеҠјдәәж•…еұ…еҸӮи§ӮгҖӮе·ҙйҮ‘жӣҫиҜҙпјҡвҖңеҸӘжңүд»–вҖҳжқҺеҠјдәәвҖҷжүҚжҳҜжҲҗйғҪзҡ„еҺҶеҸІгҖӮвҖқеңЁжқҺеҠјдәәж•…еұ…зҡ„иҸұзӘ е°ҸйҷўпјҢжҲ‘жҖҖзқҖеҙҮ敬зҡ„еҝғжғ…еҸӮи§ӮдәҶжқҺеҠјдәәж•…еұ…зәӘеҝөйҰҶзҡ„еҗ„з§Қзү©е“ҒпјҢеҗҢж—¶жғіиө·дәҶвҖңе®•жё еӣӣеӯҗвҖқзҡ„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гҖҒжқЁзү§иҖҒеёҲгҖҒжқҺеӯҰжҳҺиҖҒеёҲпјҢжҚ®иҜҙ他们зҡ„ж•…еұ…е·ІиҚЎз„¶ж— еӯҳпјҢйҒ—жҶҫгҖҒеҝғз–јгҖӮе‘Ёе•ёеӨ©иҖҒеёҲзҡ„ж•…еұ…еҗ¬иҜҙвҖңд№ҹи®ёеңЁвҖқгҖӮ第дәҢеӨ©пјҢжҲ‘еңЁиҮӘеӯҰгҖҠеӯҰд№ ејәеӣҪгҖӢж—¶пјҢиҜ»еҲ°д№ иҝ‘е№іжҖ»д№Ұи®°зҡ„и®ІиҜқпјҡвҖңж–ҮеҢ–жҳҜеҹҺеёӮзҡ„зҒөйӯӮпјҢеҹҺеёӮеҺҶеҸІж–ҮеҢ–йҒ—еӯҳжҳҜеүҚдәәжҷәж…§зҡ„з§Ҝж·ҖпјҢжҳҜеҹҺеёӮеҶ…ж¶өгҖҒе“ҒиҙЁгҖҒзү№иүІзҡ„йҮҚиҰҒж Үеҝ—гҖӮиҰҒеҰҘе–„еӨ„зҗҶеҘҪдҝқжҠӨе’ҢеҸ‘еұ•зҡ„е…ізі»пјҢжіЁйҮҚеҹҺеёӮеҺҶеҸІж–Үи„үпјҢеғҸеҜ№еҫ…вҖҳиҖҒдәәвҖҷдёҖж ·е°ҠйҮҚе’Ңе–„еҫ…еҹҺеёӮдёӯзҡ„иҖҒе»әзӯ‘пјҢдҝқз•ҷеҹҺеёӮеҺҶеҸІж–ҮеҢ–и®°еҝҶпјҢи®©дәә们记еҫ—дҪҸеҺҶеҸІгҖҒи®°еҫ—дҪҸд№Ўж„ҒпјҢеқҡе®ҡж–ҮеҢ–иҮӘдҝЎпјҢеўһејә家еӣҪжғ…жҖҖгҖӮвҖқжҲ‘еҸҲжғіиө·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жқҘгҖӮеҜ№дәҺ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еңЁе…ЁеӣҪж–Үеқӣзҡ„еҪұе“ҚеҠӣпјҢдёӯеӣҪзӨҫдјҡ科еӯҰйҷўеңЁ2018е№ҙ1жңҲ30ж—Ҙз»ҷдёӯе…ұдёӯеӨ®еҠһе…¬еҺ…дёҖд»Ҫдё“дҫӣдҝЎжҒҜдёӯжӣҫе°ұд»–зҡ„гҖҠд№Ўжқ‘еҝ—гҖӢжҢҮеҮәпјҡиҙәдә«йӣҚвҖңд»ҘеҚҒеҚ·жң¬гҖҒдёүзҷҫдҪҷдёҮеӯ—зҡ„йёҝзҜҮе·ЁеҲ¶зҡ„дҪ“йҮҸпјҢд»ҺеҶңжқ‘еңҹең°еҸҳйқ©гҖҒд№Ўжқ‘ж”ҝжІ»гҖҒж°‘дё»жі•еҲ¶зӯүж¶үеҸҠд№Ўжқ‘з”ҹжҙ»зҡ„еҗ„дёӘж–№йқўпјҢжү“йҖ жҲҗд№Ўеңҹзі»еҲ—е°ҸиҜҙпјҢиҝҷеңЁдёӯеӣҪзҺ°д»ЈгҖҒеҪ“д»Јд№Ўеңҹж–ҮеӯҰеҸІдёҠпјҢеҸҜд»ҘиҜҙеҮ д№ҺжҳҜзӢ¬дёҖж— дәҢзҡ„гҖӮвҖқвҖңиҝҷж ·зҡ„еҶҷдҪңжҠұиҙҹеҫҲеғҸжҹійқ’пјҢеңЁиҙәдә«йӣҚгҖҠд№Ўжқ‘еҝ—гҖӢе°ҸиҜҙйҮҢпјҢжҲ‘们зңӢеҲ°дәҶжҹійқ’гҖҠеҲӣдёҡеҸІгҖӢзҡ„еҶҷдҪңжҲҗе°ұеңЁеҪ“дёӢзҡ„жңҖеҘҪзҡ„继жүҝд»ҘеҸҠж–°зҡ„з”ҹй•ҝзӮ№гҖӮвҖқвҖңиҙәдә«йӣҚд№Ўеңҹе°ҸиҜҙжңүдёҖдёӘжҳҫи‘—зҡ„зү№зӮ№пјҡд№Ўжқ‘з”ҹжҙ»з»ҸйӘҢгҖҒеҶ…зҪ®зҡ„д№Ўжқ‘и§ҶзӮ№пјҢе…¶е°ҸиҜҙж—ўеҸҜд»Ҙз»ҷеҶңж°‘зңӢпјҢд№ҹеҸҜд»Ҙз»ҷеҹҺйҮҢдәәе’ҢзҹҘиҜҶеҲҶеӯҗзңӢпјҢиҝҷеңЁеҪ“еүҚд№Ўеңҹе°ҸиҜҙеҶҷдҪңдёӯжҳҫеҫ—еҮӨжҜӣйәҹи§’вҖқгҖӮпјҲи§ҒдёӯеӣҪзӨҫдјҡ科еӯҰйҷўгҖҲиҰҒжҠҘгҖү第дёҖдәҢе…«жңҹгҖҠеҸ‘еұ•д№Ўеңҹж–ҮеӯҰпјҢеҠ©еҠӣд№Ўжқ‘жҢҜе…ҙгҖӢпјҢдҪңиҖ…еҲҳиүігҖӮпјүз”ұжӯӨеҸҜи§Ғд»–еңЁе…ЁеӣҪд№Ўеңҹж–ҮеӯҰеҲӣдҪңдёӯзҡ„еҪұе“Қе’Ңең°дҪҚгҖӮд»–зҡ„дәәз”ҹз»ҸеҺҶгҖҒд»–зҡ„еҲӣдҪңйҒ“и·ҜгҖҒд»–зҡ„е®қиҙөзІҫзҘһпјҢжҳҜеҖјеҫ—жҲ‘们еӯҰд№ е’Ңж·ұжҖқзҡ„гҖӮ

д№ҰдҝЎеҫҖжқҘ
вҖңиӢҰйҡҫжҳҜеӨ©жүҚзҡ„ж‘ҮзҜ®пјҒвҖқ
жі•еӣҪи‘—еҗҚзҡ„дәәйҒ“дё»д№үдҪң家зҪ—жӣјВ·зҪ—е…°иҝҷеҸҘеҗҚиЁҖпјҢжҳҜ36е№ҙеүҚ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йҖҡиҝҮд№ҰдҝЎеҶҷз»ҷжҲ‘зҡ„гҖӮ
з»ҸжҲ‘еүҚж®өж—¶й—ҙжҹҘйҳ…иө„ж–ҷпјҢзЎ®е®ҡжҲ‘жҳҜ1еІҒеҚҠж—¶еӨұеҺ»зҲ¶жҜҚпјҢз”ұе©Ҷе©ҶжҠҡе…»й•ҝеӨ§гҖӮжҲ‘д»Һе°ҸеҜ№ж•°еӯ—дёҚеӨӘж•Ҹж„ҹпјҢеҜ№ж–Үеӯ—йўҮж„ҹе…ҙи¶ЈпјҢеӨ§жҰӮе°ұжҳҜеӨ©иөӢеҗ§гҖӮйӮЈж—¶е®¶ж— и—ҸзІ®пјҢжӣҙж— и—Ҹд№ҰпјҢ家еҫ’еӣӣеЈҒгҖӮж №жң¬ж— й’ұд№°д№ҰпјҢйҷӨдәҶиҜҫжң¬д№ҰеӨ–пјҢиҰҒжғіеӯҰд№ пјҢжҲ‘е°ұеңЁз”ҹдә§йҳҹйӣҶдҪ“йқўжҲҝйҮҢжүҫеҢ…жҢӮйқўзҡ„д№ҰжҠҘжқҘиҜ»гҖӮдёҠеҲқдёӯдёҖе№ҙзә§ж—¶пјҢзңӢдәҶдёҖдәӣз”өеҪұпјҢеҗ¬дәҶдёҖдәӣж°‘й—ҙж•…дәӢпјҢе°ұжңүдәҶеҶҷдҪңж•…дәӢзҡ„еҶІеҠЁгҖӮ1982е№ҙпјҢеҺҝеӣҫд№ҰйҰҶиөөжіҪиҠіе…Ҳз”ҹжқҘж–ҮеҙҮд№Ўдёӯеҝғж Ўи®Ійқ©е‘Ҫж•…дәӢпјҢд»–дҪңдёәдёҖдҪҚиҖҒең°дёӢе…ҡе‘ҳпјҢжҲҗдәҶжҲ‘еҝғзӣ®дёӯзҡ„иӢұйӣ„пјҢеҙҮжӢңзҡ„еҒ¶еғҸгҖӮзЎ®е®һжІЎеҗҢд»–жү“иҝҮдёҖеҸҘжӢӣе‘јпјҢд№ҹжІЎжңүдәәд»Ӣз»Қе’Ңд»–и®ӨиҜҶпјҢжӣҙдёҚжІҫдәІеёҰж•…гҖӮжҲ‘д№ҹдёҚзҹҘе“ӘйҮҢжқҘзҡ„еӢҮж°”пјҢжҮөжҮөжҮӮжҮӮең°з”ЁдҪңж–ҮзәёжҠ„дәҶдёҖзҜҮиҜӯж–ҮиҖҒеёҲеңЁиҜҫе ӮдёҠиЎЁжү¬иҝҮжҲ‘зҡ„дҪңж–ҮпјҢдёҚзҹҘеӨ©й«ҳең°еҺҡең°з»ҷиөөжіҪиҠіе…Ҳз”ҹеҜ„еҺ»гҖӮиҝҷе°ұжҳҜжҲ‘дәәз”ҹзҡ„第дёҖж¬ЎжҠ•зЁҝгҖӮжІЎжғіеҲ°пјҢиөөжіҪиҠіе…Ҳз”ҹеҫҲеҝ«еӣһдҝЎпјҢдҝЎзҡ„еҶ…е®№еӨ§жҰӮжҳҜиҜҙжҲ‘жҳҜзҘ–еӣҪзҡ„иҠұжңөпјҢзЁҝ件已收еҲ°пјҢе·ІиҪ¬еҲ°жё еҺҝж–ҮиүәеҲӣдҪңеҠһе…¬е®ӨпјҲз®Җз§°вҖңеҺҝеҲӣеҠһвҖқпјүпјҢд»ҠеҗҺжҲ‘еҰӮиҰҒжҠ•зЁҝпјҢиҜ·еҜ„з»ҷ他们гҖӮиҷҪ然第дёҖзҜҮдҪңж–ҮжңӘеҸҳжҲҗжўҰеҜҗд»ҘжұӮзҡ„й“…еӯ—пјҢдҪҶзқҖе®һд»ӨжҲ‘е…ҙеҘӢдәҶи®ёд№…гҖӮд»ҺжӯӨпјҢжҲ‘ејҖе§Ӣеҗ‘еҺҝеҲӣеҠһжҠ•зЁҝпјҢеҲҳеҸӢиҒ”гҖҒжқҺйҡҶзӮҺиҖҒеёҲзӣёз»§зҹӯжҡӮз»ҷжҲ‘ж”№зЁҝеӣһдҝЎгҖӮйҡҸеҚіпјҢйғ‘жҒ¬дё»д»»жҜҸеӯЈеәҰжҢүж—¶з»ҷжҲ‘еҜ„жқҘгҖҠжё жұҹж–ҮиүәгҖӢжқӮеҝ—гҖӮ1984е№ҙеҲқпјҢзӣҙжҺҘз”ұ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з»ҷжҲ‘д№ҰдҝЎиҫ…еҜјпјҢ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з»ҷжҲ‘иҫ…еҜјж—¶й—ҙжңҖй•ҝпјҢиҫ…еҜјеҫ—еҫҲз»ҶиҮҙгҖӮ
дәә们常иҜҙпјҡвҖңжІЎжңүж— зјҳж— ж•…зҡ„зҲұпјҢд№ҹжІЎжңүж— зјҳж— ж•…зҡ„жҒЁвҖқгҖӮжғіжғіжҲ‘е’Ң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зҡ„дәәз”ҹдәӨйӣҶпјҢд№ҹжҳҜеҒ¶з„¶дёӯзҡ„еҝ…然гҖӮ1983е№ҙдёӢеҚҠе№ҙпјҢеҺҝдёҠдё“й—ЁжҲҗз«ӢдәҶвҖңж–ҮиүәеҲӣдҪңеҠһе…¬е®ӨвҖқпјҢгҖҠжё жұҹж–ҮиүәгҖӢз”ұж–ҮеҢ–йҰҶдё»еҠһиҪ¬еҲ°еҺҝеҲӣеҠһдё»еҠһпјҢеҪ“ж—¶еҲӣеҠһеҸӘжңүйғ‘жҒ¬дё»д»»вҖңе…үжқҶеҸёд»ӨвҖқдёҖдәәгҖӮ1984е№ҙжҳҘиҠӮеҲҡиҝҮпјҢ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д»ҺеұҸиҘҝе…¬зӨҫж–ҮеҢ–з«ҷеҖҹи°ғеҲ°еҺҝеҲӣеҠһпјҢдёҖиҫ№еҒҡгҖҠжё жұҹж–ҮиүәгҖӢиҙЈд»»зј–иҫ‘пјҢдёҖиҫ№з»§з»ӯд»ҺдәӢиҮӘе·ұзҡ„ж–ҮиүәеҲӣдҪңгҖӮ
гҖҠжё жұҹж–ҮиүәгҖӢжҳҜдёҠдё–зәӘ80е№ҙд»Јжё еҺҝжңҖжқғеЁҒзҡ„ж–ҮеӯҰеҲҠзү©пјҢеҘ№иҷҪ然еҸӘжҳҜдёҖжң¬еҺҝзә§еҶ…йғЁж–ҮиүәеҲҠзү©пјҢеҸҜеңЁеҪ“ж—¶жҲ‘们иҝҷдәӣж–ҮеӯҰзҲұеҘҪиҖ…зңјйҮҢпјҢе…¶ең°дҪҚ并дёҚдәҡдәҺгҖҠдәәж°‘ж–ҮеӯҰгҖӢгҖҒгҖҠеҪ“д»ЈгҖӢзӯүгҖӮеңЁжҲ‘иҝҳжІЎжӯЈејҸеҗ‘гҖҠжё жұҹж–ҮиүәгҖӢжҠ•зЁҝд№ӢеүҚпјҢе°ұеңЁгҖҠжё жұҹж–ҮиүәгҖӢдёҠиҜ»еҲ°дәҶ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гҖҠжҲ‘зҡ„зҒ°еёҲеӮ…гҖӢгҖҠдә”жңҲдәәеҖҚеҝҷгҖӢзӯүдҪңе“ҒпјҢдҪңе“ҒдёӯйӮЈдәӣз”ҹеҠЁзҡ„ж•…дәӢе’Ңдәәзү©еҪўиұЎпјҢд»ҘеҸҠж•ЈеҸ‘еҮәзҡ„жө“жө“зҡ„жіҘеңҹж°”жҒҜпјҢдёҚдҪҶеј•иө·дәҶжҲ‘иҝҷдёӘеҶңж°‘зҡ„е„ҝеӯҗзЁҡе«©еҝғзҒөзҡ„ејәзғҲе…ұйёЈпјҢеҜ№жҲ‘иө·еҲ°дәҶжҪң移й»ҳеҢ–зҡ„дҪңз”ЁпјҢеҪұе“ҚжһҒж·ұгҖӮиҖҢдё”еңЁжҲ‘еҝғйҮҢж ‘з«Ӣиө·дәҶдёҖдёӘй«ҳеӨ§зҡ„зІҫзҘһеҒ¶еғҸпјҢе°Ҫз®ЎжҲ‘йӮЈж—¶е’Ң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иҝҳж— зјҳи§ҒйқўгҖӮ
жҲ‘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еҒҸиҝңеұұеҢәзҡ„еҶңжқ‘еЁғе„ҝпјҢиө¶еңәдёҠиЎ—зҲұеҫҖд№Ўж–ҮеҢ–з«ҷи·‘пјҢж–ҮеҙҮд№Ўж–ҮеҢ–е№ІдәӢиғЎиӢҘе…ҙе’Ң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дёҖиө·еңЁеҺҝдёҠејҖиҝҮеҮ ж¬Ўж–ҮеҢ–з«ҷе№ІдәӢзҡ„дјҡи®®пјҢеҗ¬жҲ‘жҸҗеҲ°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еңЁиҫ…еҜјжҲ‘еҶҷдҪңпјҢеҮӯзқҖд»–еҜ№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зҡ„йӣ¶жҳҹдәҶи§ЈпјҢеҚіз»ҷжҲ‘и®Іпјҡиҙәдә«йӣҚд№ҹжҳҜеұҸиҘҝд№Ўзҡ„ж–ҮеҢ–е№ІдәӢпјҢ家еўғиҙ«еҜ’пјҢе°ҸеӯҰжҜ•дёҡеҗҺе°ұеӣһд№ЎеҠіеҠЁпјҢз»“е©ҡеҗҺз”ҹзҡ„еЁғеЁғжҳҜдҫҸе„’пјҢе‘ҪиҝҗеӨҡжЎҖгҖӮдҪҶд»–еҚҙзҹўеҝ—дёҚжёқпјҢеқҡжҢҒиҮӘеӯҰгҖӮвҖңж–ҮеҢ–еӨ§йқ©е‘ҪвҖқз»“жқҹпјҢеӣҪ家жҒўеӨҚй«ҳиҖғеҗҺпјҢд»–жғіеҺ»еҸӮеҠ й«ҳиҖғпјҢеҚҙеӣ еҸӘжңүе°ҸеӯҰж–ҮеҮӯиў«жӢ’д№Ӣй—ЁеӨ–гҖӮдёәдәҶе®һзҺ°иҮӘе·ұзҡ„дәәз”ҹд»·еҖјпјҢд»–иҝҷжүҚејҖе§Ӣж–ҮеӯҰеҲӣдҪңгҖӮд»–жӣҫз»ҸиҮӘеӯҰиҝҮзјқзә«пјҢеҸҲи·ҹдәәеӯҰиҝҮжіҘж°ҙе·ҘпјҲд»–зҡ„гҖҠжҲ‘зҡ„зҒ°еёҲеӮ…гҖӢе°ұжҳҜеҶҷзҡ„жіҘж°ҙе·Ҙзҡ„з”ҹжҙ»пјүгҖӮеңЁгҖҠжё жұҹж–ҮиүәгҖӢгҖҠе·ҙеұұж–ҮиүәгҖӢеҸ‘иЎЁдәҶдёҖдәӣдҪңе“ҒпјҢеҖҹи°ғеҲ°еҺҝеҲӣеҠһе·ҘдҪңгҖӮеҗ¬дәҶ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зҡ„жӣІжҠҳе’ҢдёҚе№ёзҡ„з»ҸеҺҶеҗҺпјҢжҲ‘еҜ№д»–жӣҙеҠ иӮғ然иө·ж•¬пјҢжҲ‘жӣҙеҠ д»Ҙд»–дёәжҰңж ·пјҢеҠӘеҠӣиҜ»д№ҰпјҢжҲҳиғңз”ҹжҙ»дёӯдёҖеҲҮиү°йҡҫеӣ°иӢҰгҖӮ
第дёҖж¬Ўи°Ӣйқў
жҲ‘жҠ•еҜ„з»ҷ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зҡ„зЁҝ件пјҢд»–жҳҜ件件еҝ…иҜ»пјҢзҜҮзҜҮеҝ…ж”№гҖӮд»–зҡ„еӯ—еҶҷеҫ—дёҚеӨ§пјҢеҜҶеҜҶйә»йә»пјҢдҪҶеҚҒеҲҶе·Ҙж•ҙпјҢдёҖдёқдёҚиӢҹпјҢжҳҫеҫ—еҫҲи®ӨзңҹгҖӮеҗҺжқҘжҲ‘жүҚдәҶи§ЈеҲ°пјҢз”ұдәҺд»–еңЁиҮӘеӯҰжңҹй—ҙпјҢеӣ 家еәӯеӣ°йҡҫжІЎй’ұд№°зәёпјҢиЈҒдёӢжҠҘзәёзҡ„з©әзҷҪиҫ№и§’жқҘеҒҡ笔记пјҢеӣ иҖҢе…»жҲҗдәҶжҠҠеӯ—еҶҷеҫ—еҸҲз»ҶеҸҲе°Ҹзҡ„д№ жғҜгҖӮж—¶йҡ”еӨҡе№ҙпјҢжҲ‘е·Іи®°дёҚеҫ—жҲ‘з»ҷд»–зҡ„дҝЎдёӯеҲ°еә•иҜҙдәҶд»Җд№ҲпјҢдҪҶжҲ‘еҚҙи®°еҫ—д»–еңЁз»ҷжҲ‘зҡ„еӣһдҝЎдёӯпјҢйҷӨдәҶйј“еҠұжҲ‘жҲҳиғңеӣ°йҡҫгҖҒеҠӘеҠӣеӯҰд№ е’ҢеҶҷдҪңеӨ–пјҢиҝҳж•ҷжҲ‘еҰӮдҪ•еҒҡдәәгҖӮ
1984е№ҙ6жңҲзҡ„дёҖеӨ©пјҢжҲ‘еҝҪ然д»ҺйӮ®еұҖ收еҲ°дәҶдёҖдёӘйј“йј“еӣҠеӣҠзҡ„зүӣзҡ®зәёдҝЎе°ҒпјҢжү“ејҖдёҖзңӢпјҢз«ҹжҳҜ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з»ҷжҲ‘еҜ„жқҘзҡ„дёҖжң¬гҖҠе‘Ёе…ӢиҠ№е°ҸиҜҙйӣҶгҖӢпјҢйҮҢйқўиҝҳеӨ№жңүдёҖе°Ғз»ҷжҲ‘зҡ„дҝЎгҖӮдҝЎзҡ„еҺҹж–ҮжҲ‘и®°дёҚжё…жҘҡдәҶпјҢдҪҶеӨ§ж„ҸжҳҜиҜҙпјҡвҖңе°ҸжҳҘпјҡжҲ‘еңЁиҫҫеҺҝеҸӮеҠ ж”№зЁҝдјҡпјҢйҖӣж–°еҚҺд№Ұеә—ж—¶пјҢж— ж„ҸдёӯзңӢи§Ғиҝҷжң¬гҖҠе‘Ёе…ӢиҠ№е°ҸиҜҙйӣҶгҖӢпјҢе‘Ёе…ӢиҠ№е’ҢдҪ гҖҒе’ҢжҲ‘дёҖж ·пјҢд№ҹжҳҜеҶңж°‘еҮәиә«пјҢз»ҸеҺҶд№ҹеҚҒеҲҶжӣІжҠҳпјҢжҲ‘жғіиҝҷжң¬д№ҰеҜ№дҪ еҸҜиғҪжңүеё®еҠ©пјҢзү№д№°дёӢжқҘйҖҒдҪ гҖӮж„ҝдҪ иғҪжҲҳиғңеӣ°йҡҫпјҢи®©жҲ‘们е…ұеҗҢеӯҰд№ пјҢе…ұеҗҢиҝӣжӯҘпјҒвҖқиҜ»е®ҢдҝЎпјҢй—»зқҖд№ҰйЎөдёӯж•ЈеҸ‘еҮәзҡ„ж·Ўж·ЎеўЁйҰҷпјҢжҲ‘ж„ҹеҠЁеҫ—еҸҢзңјжЁЎзіҠдәҶгҖӮе°Ҫз®ЎеҸӘжҳҜдёҖжң¬д№ҰпјҢеҸҜзӣҙеҲ°еҰӮд»ҠпјҢи§үеҫ—иҝҷжҳҜжҲ‘дәәз”ҹ收еҲ°зҡ„дёҖд»ҪжңҖзҸҚиҙөзҡ„зӨјзү©гҖӮйӮЈж—¶жҲ‘е’Ңд»–иҝҳжІЎи§ҒйқўпјҢеҸӘжҳҜдә’зӣёйҖҡиҝҮеҮ ж¬ЎдҝЎпјҢд»–еҚҙз»ҷжҲ‘д№°жқҘд№ҰйҖҒжҲ‘пјҢеҜ№дәҺеҪ“ж—¶дёҖдёӘеӯҰз”ҹеЁғеЁғпјҢеҸҜд»ҘжғіеғҸиҝҷз§Қйј“еҠұжңүеӨҡеӨ§гҖӮдҪ•еҶөжҲ‘еҪ“ж—¶е·Із»ҸзҹҘйҒ“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зҡ„家еўғ并дёҚеҘҪпјҢжҜҸж¬Ўд»ҺеұҸиҘҝеҲ°жё еҹҺеҠһдәӢйғҪжҳҜиө°и·ҜпјҢиҝһиҪҰд№ҹиҲҚдёҚеҫ—еқҗпјҢеҚҙжғҰи®°зқҖжҲ‘зҡ„жҲҗй•ҝ并жҺҸй’ұз»ҷжҲ‘д№°д№ҰпјҢиҝҷд»ҪеҸӢи°ҠеҸҲжҳҜеӨҡд№ҲејҘи¶ізҸҚиҙөгҖӮжҲ‘зҹҘйҒ“иҙәиҖҒеёҲеҜ№жҲ‘еҜ„жүҳдәҶеҫҲеӨ§зҡ„еёҢжңӣпјҢд»ҺжӯӨд»ҘеҗҺж— и®әеңЁеӯҰд№ е’ҢеҶҷдҪңдёҠпјҢжҲ‘йғҪжӣҙдёҚж•ўжҮҲжҖ гҖӮ
1984е№ҙ8жңҲ10ж—ҘпјҢеҲҡеҲҡж”ҫзүӣеӣһ家зҡ„жҲ‘收еҲ°жқҘиҮӘеҺҝеҲӣеҠһзҡ„дјҡи®®йҖҡзҹҘпјҢиҜ·жҲ‘еҸӮеҠ вҖңжё еҺҝйҰ–еұҠзҹӯзҜҮе°ҸиҜҙеҲӣдҪңеә§и°ҲдјҡвҖқгҖӮеҗҺжқҘеҫ—зҹҘжҳҜ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жһҒеҠӣеҗ‘йғ‘жҒ¬дё»д»»жҺЁиҚҗжҲ‘пјҢз»ҷжҲ‘дәҶдәәз”ҹдёӯ第дёҖж¬Ўж–ҮеӯҰеҲӣдҪңеӯҰд№ зҡ„жңәдјҡгҖӮ
жҲ‘е©Ҷе©Ҷд№ҹиҖғиҷ‘еҲ°жӯӨдәӢеҜ№жҲ‘жқҘиҜҙйқһеҗҢе°ҸеҸҜпјҢд№җж„Ҹи®©жҲ‘еҸӮеҠ гҖӮеңЁеҗ‘йӮ»еұ…еҖҹиҪҰиҲ№иҙ№ж— жһңзҡ„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еҘ№жҠҠ家дёӯеҮҶеӨҮеҒҡе‘·й…’зҡ„й«ҳзІұиғҢеҲ°ж–ҮеҙҮиЎ—дёҠеҚ–дәҶпјҢж…·ж…Ёең°з»ҷжҲ‘еҒҡи·Ҝиҙ№гҖӮдёҖи·Ҝйў з°ёжқҘеҲ°жё еҺҝеҹҺпјҢеңЁжё еҺҝеӨ§ж—…йҰҶжҠҘеҲ°гҖӮи§ҒеҲ°дәҶжңқжҖқжҡ®жғізҡ„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пјҢжҲ‘жӣҫжғіеғҸд»–й«ҳеӨ§дёҠпјҢеҚҙи§Ғд»–дёӯзӯүиә«жқҗпјҢи“„зқҖе№іеӨҙпјҢдёҖдҪҚе…ёеһӢзҡ„еҶңжқ‘жұүеӯҗеҪўиұЎгҖӮйқһеёёжңҙзҙ пјҢе’Ңи”јеҸҜдәІгҖӮд»–еҜ№жҲ‘еҳҳеҜ’й—®жҡ–пјҢжҠ‘жү¬йЎҝжҢ«зҡ„иҜқиҜӯдёӯйҖҸеҮәдәҶж— е°Ҫзҡ„е…іеҝғе’Ңе…ізҲұгҖӮ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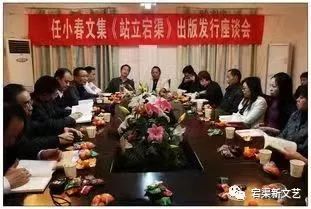
еҸ‘иЎЁеӨ„еҘідҪң
еҸӮеҠ еә§и°Ҳдјҡзҡ„жңүйғ‘жҒ¬гҖҒйӮ“еӨ©жҹұгҖҒжӣҫдјҹгҖҒжқЁж–№и·ғгҖҒ欧йҳіеҶӣгҖҒйҷҲе№ігҖҒйғӯжғ ж°‘гҖҒйҫҷжҮӢеӢӨгҖҒй»„ж–Үеі°гҖҒеј дёҪзӯүзӯүпјҢ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иҮӘ然дёҚдҫӢеӨ–пјҢд»–еҗҢж—¶иҝҳиҰҒдёәдјҡеҠЎеҝҷйҮҢеҝҷеӨ–гҖӮеә§и°ҲдјҡдёҘиӮғгҖҒзҙ§еј гҖҒзғӯзғҲпјҢйҷӨжҲ‘жҳҜдёӘвҖңжҲҙзқҖзәўйўҶе·ҫзҡ„еӯҰз”ҹвҖқжңӘеҸ‘иЎЁиҝҮдёҖдёӘй“…еӯ—зҡ„еҲқеӯҰиҖ…еӨ–пјҢ他们йғҪжҳҜжңүеӨ§йҮҸдҪңе“ҒеҸ‘иЎЁзҡ„жё еҺҝж–ҮеӯҰз•Ңзҡ„йӘЁе№ІгҖӮ
еә§и°ҲдјҡдёҠпјҢ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жҺЁеҮәдәҶжҲ‘зҡ„еҜ“иЁҖејҸе°ҸиҜҙгҖҠзәўйңһгҖӢеҸӮеҠ и®Ёи®әгҖӮеҗ„дҪҚиҖҒеёҲй’ҲеҜ№дҪңе“Ғзҡ„дёҚи¶іпјҢиҜҡжҒіең°жҸҗеҮәдәҶдҝ®ж”№ж„Ҹи§ҒгҖӮжҲ‘д»Һе°ҸиҮӘз”ұж•Јжј«жғҜдәҶпјҢе“Әи§ҒиҝҮиҝҷз§Қйҳөд»—пјҢдёҚз”ұеҫ—вҖңе“ҮвҖқең°дёҖеЈ°еӨ§е“ӯиө·жқҘгҖӮйғ‘жҒ¬дё»д»»е’Ң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и§ҒеҠҝдёҚеҰҷпјҢ马дёҠжҠҠжҲ‘еҸ«еҮәпјҢиҜӯйҮҚеҝғй•ҝең°еҠқи§Јиө·жҲ‘жқҘгҖӮ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зү№еҲ«е®үж…°жҲ‘пјҡвҖңдёҖеҲҮйғҪжҳҜжӯЈеёёзҡ„пјҢеҝ иЁҖйҖҶиҖіеҲ©дәҺиЎҢпјҢиүҜиҚҜиӢҰеҸЈеҲ©дәҺз—…гҖӮдҪ еҘҪеҘҪеҗ¬иҖҒеёҲ们зҡ„ж„Ҹи§ҒпјҢдҪ жҳҜжңҖжЈ’зҡ„пјҒвҖқеә§и°ҲдјҡпјҢејҖдәҶдёҖе‘ЁпјҢжҲ‘йқҷдёӢеҝғжқҘе®һе®һеңЁеңЁеӯҰеҲ°дәҶи®ёеӨҡдёңиҘҝгҖӮжңҹй—ҙпјҢ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иҝҳеёҰйўҶжҲ‘们еҸӮи§ӮдәҶжӯЈеңЁе»әи®ҫдёӯзҡ„жё жұҹеӨ§жЎҘгҖӮ
еңЁеӣһд№Ўд№ӢеүҚпјҢ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еңЁеҺҝеҲӣеҠһз»ҷжҲ‘и§ЈеҶідәҶеҫҖиҝ”и·Ҝиҙ№пјҢиҝҳз»ҷжҲ‘еҸ‘дәҶиҜҜе·ҘиЎҘеҠ©гҖӮеҸӮеҠ иҝҷж¬Ўеә§и°ҲдјҡдёҚдҪҶи®ӨиҜҶдәҶдёҖжү№ж–ҮеӯҰиҖҒеёҲпјҢеӯҰеҲ°дәҶдёҖдәӣж–ҮеӯҰзҹҘиҜҶпјҢиҝҳиөҡдәҶиҜҜе·ҘиЎҘиҙҙпјҢжҲ‘й«ҳе…ҙжһҒдәҶгҖӮ
дёҚд№…пјҢжҲ‘зҡ„еҜ“иЁҖејҸе°ҸиҜҙгҖҠзәўйңһгҖӢеҸ‘иЎЁеңЁгҖҠжё жұҹж–ҮиүәгҖӢвҖңзәӘеҝөе»әеӣҪ35е‘Ёе№ҙвҖқдё“еҲҠеҸ·дёҠгҖӮеҪ“жҲ‘收еҲ°йӮЈжңҹжқӮеҝ—зҡ„ж—¶еҖҷпјҢгҖҠжё жұҹж–ҮиүәгҖӢйӮЈ4дёӘзәўиүІеӨ§еӯ—е’ҢеҸҳжҲҗй“…еӯ—зҡ„гҖҠзәўйңһгҖӢпјҢиҮід»Ҡд»ӨжҲ‘и®°еҝҶзҠ№ж–°гҖӮеҪ“е№ҙпјҢжҲ‘зҡ„第дәҢзҜҮе°ҸиҜҙгҖҠеё®еҠ©гҖӢеҸ‘иЎЁпјҢдёӨзҜҮе°ҸиҜҙйғҪжҳҜ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зј–иҫ‘зҡ„гҖӮ
зӣҙеҲ°зҺ°еңЁпјҢжҲ‘йғҪеҚҒеҲҶжҖҖеҝөдёҠдё–зәӘе…«еҚҒд»Јзҡ„еҲӣдҪңж°ӣеӣҙпјҢзңҹиҜҡзҡ„еёҲз”ҹе…ізі»пјҢе’Ңи°җзҡ„еҲӣдҪңзҺҜеўғпјҢзӣёдә’жҝҖеҠұзҡ„гҖҒжҳӮжү¬зҡ„еҲӣдҪңзғӯжғ…пјҢеҸӘеҸҜжғңпјҢе•Ҷе“Ғз»ҸжөҺзҡ„еӨ§жҪ®еҫҲеҝ«е°ұе°Ҷиҝҷз§ҚзҸҚиҙөзҡ„ж—¶д»ЈеҶІеҫ—дёғйӣ¶е…«иҗҪдәҶгҖӮ

жё еҺҝеҚҒеӨ§жқ°еҮәйқ’е№ҙ
жҲ‘еҲқдёӯжҜ•дёҡиҖғдёҠж¶Ңе…ҙдёӯеӯҰй«ҳдёӯйғЁпјҢзҡ„зҡ„确确家иҙ«ж— иө„пјҢеҸӘжңүеӣһд№ЎеҠЎеҶңдәҶгҖӮиҖҢйӮЈж—¶пјҢ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д№ҹзҰ»ејҖдәҶеҺҝеҲӣеҠһпјҢйҮҚж–°еӣһеҲ°д»–зҡ„иҖҒ家еұҸиҘҝд№Ўж–ҮеҢ–з«ҷпјҢжҲ‘们е°ұжёҗжёҗең°еӨұеҺ»дәҶиҒ”зі»гҖӮеӣ дёәж–ҮеҙҮдҝЎжҒҜиҫғдёәй—ӯеЎһпјҢеҠ д№ӢжҲ‘ж— иө„йҮ‘иҙӯд№°д№ҰеҲҠгҖӮд»…д»…д»ҺгҖҠжё жұҹж–ҮиүәгҖӢе’ҢгҖҠе·ҙеұұж–ҮиүәгҖӢдёҠиҜ»еҲ°дёҖдәӣ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дҪңе“ҒпјҢеҠ д№Ӣе•Ҷе“Ғз»ҸжөҺеӨ§жҪ®еҜ№ж–ҮеӯҰзҡ„еҶІеҮ»пјҢжҲ‘зҡ„дёҡдҪҷзҲұеҘҪе°ұд»Һж–ҮиүәеҶҷдҪңиҪ¬дёәж–°й—»жҠҘйҒ“гҖӮ
1989е№ҙпјҢжҲ‘еӣ иҗҪжҰңдёҚиҗҪеҝ—пјҢиҮӘеӯҰжҲҗжүҚпјҢдёҡдҪҷйҮҮеҶҷеҸ‘иЎЁж–°й—»зЁҝ件500дҪҷзҜҮпјҢиў«иҜ„дёәж”№йқ©ејҖж”ҫеҚҒе№ҙвҖңжё еҺҝеҚҒеӨ§жқ°еҮәйқ’е№ҙвҖқд№ӢдёҖгҖӮ
еңЁиҝӣжё еҺҝеҹҺеҸӮеҠ иЎЁеҪ°еӨ§дјҡжҠҘеҲ°ж—¶пјҢж¬Је–ңең°д»ҺжҠҘеҲ°еҗҚеҶҢдёҠзңӢеҲ°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зҡ„еҗҚеӯ—пјҢжҲ‘ж¬Је–ңеҰӮзӢӮпјҢ马дёҠи·‘еҲ°д»–зҡ„еҜқе®ӨйҮҢжүҫд»–гҖӮеҲҶеҲ«6е№ҙпјҢз»ҲдәҺйҮҚйҖўеңЁжё еҺҝзҡ„еӨ§ж—…йҰҶйҮҢгҖӮйӮЈжҷҡпјҢжҲ‘жүҚиҜҰз»ҶзҹҘйҒ“дәҶд»–зҡ„дәәз”ҹе’Ңз»ҸеҺҶгҖӮ
еңЁгҖҠжё жұҹж–ҮиүәгҖӢзј–иҫ‘йғЁжңҹй—ҙпјҢ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еҲӣдҪңдәҶгҖҠдә”жңҲдәәеҖҚеҝҷгҖӢгҖҠеҘҪдәӢеӨҡзЈЁгҖӢгҖҠиңңжңҲпјҢ并дёҚйғҪжҳҜз”ңзҡ„гҖӢзӯүе°ҸиҜҙгҖӮ1985е№ҙпјҢеңЁгҖҠзҺ°д»ЈдҪң家гҖӢеҸ‘иЎЁгҖҠиҠұиҠұиҪҝе„ҝеҮәеұұжқҘгҖӢпјҢж №жҚ®е°ҸиҜҙж”№зј–зҡ„е·қеү§гҖҠдҪіжңҹгҖӢиҺ·еҫ—вҖңеӣӣе·қзңҒе·қеү§еҲӣдҪңеҘ–вҖқгҖӮеҪ“е№ҙ10жңҲпјҢд»–жҲҗдәҶеҺҝз”өеӨ§з«ҷз»ҷеӯҰе‘ҳжү№ж”№дҪңж–Үзҡ„иҮӘеӯҰи§Ҷеҗ¬з”ҹпјҢжҲҗдәҶеҺҝз”өеӨ§з«ҷзҡ„иҫ…еҜјиҖҒеёҲе…јеӯҰе‘ҳгҖӮ1988е№ҙпјҢ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еҸ–еҫ—дәҶеӣӣе·қе№ҝж’ӯз”өи§ҶеӨ§еӯҰдёӯж–Үзі»дё“дёҡжҜ•дёҡиҜҒд№ҰпјҢдҫҝз”ұе°ҸеӯҰз”ҹдёҖи·ғжҲҗдёәдәҶеӨ§дё“з”ҹгҖӮ1987е№ҙпјҢжҳҜ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зҡ„еҲӣдҪң丰收е№ҙпјҢ5жңҲпјҢгҖҠеӨ©жҙҘж–ҮеӯҰгҖӢеӨҙжқЎжҺЁеҮәд»–зҡ„дёӨзҜҮе°ҸиҜҙгҖҠжІіиЎ—гҖӢгҖҠеҪ©з”»гҖӢпјӣ7жңҲпјҢгҖҠзҺ°д»ЈдҪң家гҖӢеҸ‘иЎЁдәҶд»–зҡ„е°ҸиҜҙгҖҠжңҖеҗҺдёҖж¬ЎзӨҫзҘӯгҖӢпјҢдёҚд№…пјҢеҸҲеҸ‘иЎЁдәҶгҖҠйғ‘家ж№ҫзҡ„еӯҗеӯҷгҖӢпјҢеңЁе…ЁеӣҪж–ҮеӯҰз•Ңеј•иө·дәҶејәзғҲеҸҚе“ҚгҖӮд»–еҪ“д№Ӣж— ж„§ең°иҚЈиҺ·вҖңжё еҺҝеҚҒеӨ§жқ°еҮәйқ’е№ҙвҖқд№ӢдёҖгҖӮ

жҰңж ·еҠӣйҮҸ
дәӢеңЁдәәдёәгҖӮжҲҗеҠҹеҶідёҚжҳҜеҒ¶з„¶гҖӮ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д»ҺдёҖдёӘеҶң家еӯҗејҹпјҢзӣҙзҷҪең°иҜҙпјҢд»ҺдёҖдёӘжіҘз“Ұе·ҘжҲҗй•ҝдёәдёҖеҗҚе…ЁеӣҪзҹҘеҗҚдҪң家дёҚжҳҜеҒ¶з„¶гҖӮжҲ‘иҮӘ然еҸ—еҲ°д»–жҪң移й»ҳеҢ–зҡ„еҪұе“ҚпјҢжҲ‘们иҷҪ然дәӨеҫҖдёҚеӨҡпјҢдҪҶжҳҜд»–жҳҜжҲ‘еӯҰд№ зҡ„жҰңж ·гҖҒиЎҢеҠЁзҡ„жҢҮеҚ—гҖӮ1990е№ҙпјҢжҲ‘д№ҹз”ұдёҖеҗҚеҲқдёӯз”ҹиҖғе…Ҙеӣӣе·қе№ҝж’ӯз”өи§ҶеӨ§еӯҰжё еҺҝз”өеӨ§з«ҷжұүиҜӯиЁҖж–ҮеӯҰдё“дёҡпјҢеҪ“ж—¶иҝҳжҳҜзҸӯй•ҝгҖӮеҸҜжғңзҡ„жҳҜпјҢеӯҰд№ дёҖе№ҙеҗҺпјҢжҲ‘еӣ 家еәӯеҶҚйҒӯеҸҳж•…пјҢз”ҹжҙ»йҷ·е…Ҙж°ҙж·ұзҒ«зғӯдёӯпјҢиҫҚеӯҰжү“е·ҘгҖӮеңЁжү“е·Ҙжңҹй—ҙпјҢеҢ…жӢ¬еҗҺжқҘиҝ”д№ЎеҠһеӯҰжңҹй—ҙпјҢдёҖзӣҙжІЎжңүж”ҫејғеҶҷдҪңпјҢж–ӯж–ӯз»ӯз»ӯеҸ‘иЎЁдәҶи®ёеӨҡж–ҮиүәдҪңе“ҒгҖӮжёҗжёҗең°пјҢжңүдәҶжҠҠж–Үз« йӣҶз»“еҮәзүҲзҡ„ж„ҝжңӣгҖӮ2010е№ҙпјҢжҲ‘зҡ„第дёҖйғЁдҪңе“ҒйӣҶгҖҠд»Һе·ҙжІіеҲ°жё жұҹгҖӢеҚ°еҲ·еҮәзүҲеҗҺпјҢжҲ‘иҮӘ然е…ҙеҢҶеҢҶең°з»ҷ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иө йҖҒдёҖжң¬гҖӮд»–еңЁиөһи®ёзҡ„еҗҢж—¶пјҢе®һе®һеңЁеңЁз»ҷжҲ‘жіјдәҶдёҖзӣҶеҶ·ж°ҙгҖӮд»–иҜҙпјҡвҖңеҮәзүҲд№ҰзұҚжҳҜеҘҪдәӢпјҢиҠӮзәҰеҮ дёӘеҮәзүҲиҙ№д№ҹеҸҜд»ҘзҗҶи§Ј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дёәдәҶзңҹжӯЈж„Ҹд№үдёҠй”ӨзӮјиҮӘе·ұпјҢд»ҺеҮәд№ҰејҖе§Ӣе°ұиҰҒеҺ»з”іиҜ·жӯЈи§„д№ҰеҸ·пјҢжүҫжӯЈи§„еҮәзүҲзӨҫпјҢдёҚиҰҒеҺ»еҘ—з”ЁеҲ«дәәзҡ„д№ҰеҸ·пјҢе…ій”®дёҚиғҪдҪ“зҺ°д№Ұзҡ„д»·еҖјгҖӮвҖқиҜҙе®һеңЁзҡ„пјҢеҪ“ж—¶жҲ‘жһҒе…¶е°ҙе°¬пјҢйқўеӯҗиҝҮдёҚеҺ»пјҢеҶ…еҝғжһҒйҡҫеҸ—гҖӮиҝҮдёҖж®өж—¶й—ҙпјҢжҲ‘еҸҚеӨҚжҖқиҖғ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зҡ„иҜқпјҢйҶҚйҶҗзҒҢйЎ¶пјҢиҢ…еЎһйЎҝејҖгҖӮеҗҺжқҘпјҢйҡҸзқҖжҲ‘гҖҠз”ҹе‘ҪйҖҡйҒ“гҖӢгҖҠжё еҺҝзҡ„жЎҘгҖӢгҖҠдҝЎВ·и®ҝгҖӢзӯүеҮәзүҲпјҢжҜҸж¬Ўж–°д№Ұеә§и°Ҳж—¶еҸӘиҰҒ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еңЁжё еҺҝд»–йғҪдјҡдәІиҮӘеҸӮеҠ пјҢ并жҸҗдёҖдәӣж„Ҹи§Ғе’Ңе»әи®®гҖӮеҗҺжқҘд»–е»әи®®жҲ‘еӨҡеҶҷдёҖдәӣй«ҳиҙЁйҮҸдҪңе“ҒпјҢдёҚиҰҒдёәеҶҷдҪңиҖҢеҶҷдҪңпјҢд№ҹдёҚиҰҒдёәж•°йҮҸиҖҢеҶҷдҪңпјҢжіЁйҮҚдҪңе“Ғзҡ„иҙЁйҮҸпјҢ并鼓еҠұжҲ‘еӨҡеҗ‘зңҒзә§д»ҘдёҠж–ҮеӯҰжҠҘеҲҠжҠ•зЁҝпјҢд»ҘжӯӨдҪңдёәеҸ‘еұ•ж–№еҗ‘пјҢжҸҗй«ҳиҮӘе·ұзҡ„еҶҷдҪңж°ҙе№ігҖӮжҲ‘欣然жҺҘеҸ—гҖӮиҝ‘еҮ е№ҙпјҢжҲ‘йҷҶйҷҶз»ӯз»ӯеңЁгҖҠеӣӣе·қж–ҮеӯҰгҖӢгҖҠеӣӣе·қдҪң家гҖӢгҖҠдёӯеӣҪдәӨйҖҡжҠҘгҖӢгҖҠдёӯеӣҪйӮ®ж”ҝжҠҘгҖӢгҖҠеӣӣе·қдәӨйҖҡгҖӢзӯүжҠҘеҲҠеҸ‘иЎЁдәҶи®ёеӨҡдҪңе“ҒгҖӮ
еҢҶеҢҶзҡ„ж—¶е…үеҰӮжўӯпјҢеІҒжңҲеҰӮжөҒгҖӮжҲ‘е’Ң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йғҪиҝӣе…ҘдәҶдёӯиҖҒе№ҙзҡ„иЎҢеҲ—пјҢд»ҠеӨ©жҲ‘иғҪжҢҘжҙ’иҮӘеҰӮең°еҸ‘жҢҘдёҡеҠЎзҲұеҘҪпјҢеҫ—зӣҠдәҺйҒҮеҲ°дәҶ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иҝҷдҪҚиүҜеёҲзӣҠеҸӢгҖӮиҷҪ然жҲ‘е’Ңиҙәдә«йӣҚиҖҒеёҲйғҪз»ҸеҺҶдәҶи®ёи®ёеӨҡеӨҡдәәз”ҹжІ§жЎ‘пјҢдҪҶжҳҜпјҢжҲ‘们зҡ„ж•…дәӢпјҢдёҚиғҪйҒ—еҝҳгҖӮд»–еҜ№жҲ‘зҡ„жғ…и°ҠпјҢж°ёиҝңй“ӯи®°гҖӮ
дҪңиҖ…з®Җд»Ӣпјҡд»»е°ҸжҳҘпјҢзҺ°дҫӣиҒҢжё еҺҝдәӨйҖҡиҝҗиҫ“еұҖпјҢеӣӣе·қзңҒдҪң家еҚҸдјҡдјҡе‘ҳпјҢе·ІеҮәзүҲдҪңе“ҒйӣҶгҖҠз”ҹе‘ҪйҖҡйҒ“гҖӢгҖҒгҖҠжё еҺҝзҡ„жЎҘгҖӢгҖҒгҖҠжҲ‘е’Ң他们зҡ„ж•…дәӢгҖӢзӯү6йғЁгҖӮ
жё еҺҝж–ҮеӯҰиүәжңҜз•ҢиҒ”еҗҲдјҡ иҚЈиӘүеҮәе“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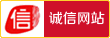 Powered by Discuz! X3.4 © 2008-2024 жё еҺҝзҪ‘ зүҲжқғжүҖжңү иңҖICPеӨҮ2021001069еҸ·-4 е·қе…¬зҪ‘е®үеӨҮ51172502000170еҸ·
жҠҖжңҜж”ҜжҢҒ: е…Ӣзұіи®ҫи®Ў
Powered by Discuz! X3.4 © 2008-2024 жё еҺҝзҪ‘ зүҲжқғжүҖжңү иңҖICPеӨҮ2021001069еҸ·-4 е·қе…¬зҪ‘е®үеӨҮ51172502000170еҸ·
жҠҖжңҜж”ҜжҢҒ: е…Ӣзұіи®ҫи®Ў